|
图书工作室 讯:
俞晓群:我喜爱的四种学术文采
我是出版人。从业三十多年来,从理科到文科,从小编辑到主持一些大型项目,接触过太多书稿,太多学者。同时我也是一个乐于写作的人,一面编书,一面学习,向作者学习,向书稿学习,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,终生志向也是在编出更好的书,写出更好的书。现在谈学术与文采问题,立刻引起我许多联想。这是一个好问题,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,我愿意谈一点自己的感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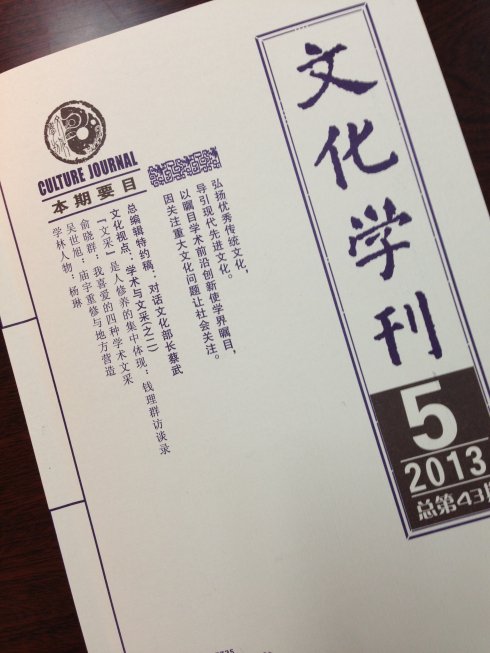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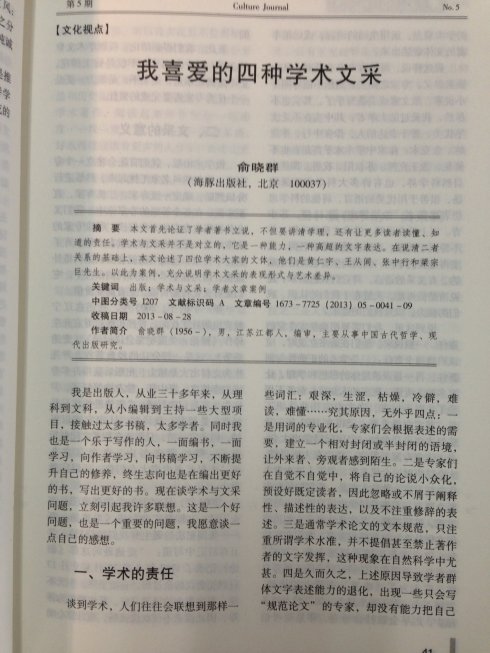
我是出版人。从业三十多年来,从理科到文科,从小编辑到主持一些大型项目,接触过太多书稿,太多学者。同时我也是一个乐于写作的人,一面编书,一面学习,向作者学习,向书稿学习,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,终生志向也是在编出更好的书,写出更好的书。现在谈学术与文采问题,立刻引起我许多联想。这是一个好问题,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,我愿意谈一点自己的感想。
一 学术的责任
谈到学术,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那样一些词汇:艰深,生涩,枯燥,冷僻,难读,难懂,……究其原因,无外乎四点:一是用词的专业化,专家们会根据表述的需要,建立一个相对封闭或半封闭的语境,让外来者、旁观者感到陌生。二是专家们在自觉不自觉中,将自己的论说小众化,预设好既定读者,因此忽略或不屑于阐释性、描述性的表达,以及不注重修辞的表述。三是通常学术论文的文本规范,只注重所谓学术水准,并不提倡甚至禁止著作者的文字发挥,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中尤甚。四是久而久之,上述原因导致学者群体文字表述能力的退化,出现一些只会写“规范论文”的专家,却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学术观点,运用生动的语言,或运用丰富的文体表述出来。
我这样说,可能有专家会反对,认为顾名思义,专家之高贵,当然不能等同于小说家、散文家或芸芸写手了。其实也不尽然,我见过的大学者,其中实在不乏文笔优美、善于表达的人,像张中行、季羡林、金克木。作家中学术水平高超者,也不鲜见,像王充闾、苏叔阳、祝勇。即使在自然科学界,也有许多大科学家文采飞扬,很善于用优美的语言,将他的科学思想表述出来,像华罗庚、王梓坤、苏步青。以上旨在说明,学术文章的风格,并不等同于枯燥、乏味、艰深那些名词,其实再难懂的学问,我们的学者也有用生动的、有文采的语言,将它们表达出来、述说清楚的可能。关键在于我们的认识、我们的能力,以及我们的追求。
说到这里,我们需要明确学术专家的责任。一般说来,他们在著书立说时,应该明确两个责任:一是学术的正确性与创新性,再一是说清楚你的思想和学理,让更多的人听懂,更多的人知道。前者不用说了,对于后者,许多专家往往认识不足。其实它很重要。记得在一九九三年,我曾经去西班牙参加一个国际科学史大会。会上许多专家的发言,很少有人听得懂。大会结束时,会议主席、美国人道本先生作总结发言,他的大意是:我们的研究有两个要点,首先是科学史研究的深入与新发现,这很重要;其次是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,这依然很重要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者,都应该重视被大众“知道”的意义。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陷入孤芳自赏,陷入为了“吃饭”而研究的境地,发展下去,圈子越来越小,知道的人越来越少,迟早会被社会唾弃,那是很可怕的。[1]
及此,我们得到结论:强调学术文章的文采,对专家而言,不仅是锦上添花,更不是画蛇添足,是水平,是能力,更是一个优秀专家需要完成的责任。
二 文采的意义
做学术出版,我们首先会建立一个专家库,将各学科名家汇拢起来,然后进行分级判断,确定一流专家、二流专家,直至末流。在各个等级的专家流中,我们又会分析哪位专家的文章好读,哪位专家的文章好看,哪位专家的文章有文采。有了这三个特点,他的书稿就会受到编辑格外重视,因为在学术水准等同的条件下,它们更有文化传播价值,更有商业价值。
举一个例子。二零零三年我还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时,曾经出版过 尹宣先生译作《辩论:美国制宪会议记录》(麦迪逊著)。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著作,尹先生为之付出大量精力,出版后获得许多专家如李慎之、资中筠、徐友渔等好评。尹宣先生在后记中写道:“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,是精品,我译时,认定它难以畅销,但必定长销,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,哪怕藏之名山,也会存之久远。”[2]但此书内容太专门化,所以印量很小。
二零零四年,易中天先生读到此书,兴奋不已,立即把它改写成《艰难的一跃——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》,并且在后记中写道:“麦迪逊的这部《辩论》记录了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,自始至终,一天不缺;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,且注释极为详尽,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,而且惊心动魄,受益良多。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,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。重讲的原因,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《辩论》,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,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,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;……我一贯认为,学术是一种好东西,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;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,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。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。我想把这段过程,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。当然,为了忠实于历史,我不能不大量引述《辩论》中的材料,……即制宪代表所有的发言,均引自尹译本《辩论》一书。……我希望这并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。”[3]结果,易先生改写的这部书立即畅销,一连出了好几版。
在这里,我们暂且放下易中天先生是否侵权的事情不论,他写文章的表述能力与文采,确实让人敬佩。他提到的“换一种表述方式”,也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文字功力。易中天先生名扬天下,除去电视等媒介炒作的因素,以及他丰富的肢体语言,他善于生动表达的文字,还是一直受到出版界的认可。由此联想,更有学术功力且更善于文字表达的学者还有很多,像钱锺书与他的《管锥编》,葛兆光与他的《中国思想史》,扬之水与她的《诗经》器物研究等,其研究对象艰深无比,但他们都能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生动明白地表达出来,写出文采,赢得读者关注,我们不能不承认,他们都有会写文章的本事。
当然,我觉得文采的意义是丰富的。谁都想将自己的文章写得像《道德经》那样精简恰当,像《论语》那样字字珠玑,像《庄子》那样妙笔生花……当代作家文字精道者寥寥无几,前有黄裳先生,后又王充闾等先生,如果我们把文章的风采局限于这样的楷模,一定会生出仰高弥坚、无法追随的慨叹。其实文章好看不仅于此,站在出版的角度,我曾经品评过几位先生的文字,有黄仁宇先生,王充闾先生,张中行先生,梁宗巨先生,他们都是善写文章的大家,都有文采,文采的表现却迥然不同。下面我把他们的故事分述如下。
三 黄仁宇的“白茉莉”
对于学术创作而言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黄仁宇先生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出现,是一个重要的事件。关注之一是人们惊叹:这样的学术书,竟然写得如此好看;关注之二是人们质疑:这样的写法,符不符合学术规范呢?
其实在海外,这样的文体并不鲜见,像史景迁的《天安门》,孔飞力的《叫魂》等。文革时期国内外隔绝,思想僵化,许多事情都受到思维模式的禁锢。而我注意黄仁宇先生的写作风格,是因为那时我正在参加三联书店“中华文库”写作,我的题目是《数术探秘》。责任编辑潘振平先生谈到写作风格时,他对我说:“虽然这套书是学术著作,但它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,强调文字的优美、完整和可读性。把引文与注释都放到每章的末尾,参考书目放到全书后,这样既可以保证著作的学术价值,又不影响读者的轻松阅读。”他接着说:“你可以看一看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。”后来的写作,我按照责任编辑的要求做了,把一排排“鱼骨刺”式的注释,都放到每章之后,文中叙述尽量避免大段引文;引文尽量转为自己的语言,融入正文的叙述之中;读者需要深究,查阅章后的注释好了。那时我只有二三十岁,这样的学术写作训练,对我一生的写作都产生重要影响。
回顾黄仁宇先生的写作过程,其实他也不是一步就达到我们今天见到的《万历十五年》那样的风格与文采。此前他花费五年时间写《明代的漕运》,并由此获密执根大学博士学位;他花费七年时间读一百三十三册《明实录》及相关资料,写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》。这些纯学术著作印量都很低,比如后者,一九七四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,仅买了八百多本。一九八五年他写《中国并不神秘》,试图从纵向上研究问题。结果出版社请专家审稿,三次都未通过。黄先生说:“他为这部书稿举行了三次葬礼。”埋葬它的人,正是大汉学家亚瑟·莱特和费正清。此事对当时年近六十岁的黄仁宇先生的自信心,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一九七六年他又写出《万历十五年》,在横向上给出中国历史的一个切片。但是,他的稿子也被英美出版商们推来推去,直至一九七八年,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,一九八一年出版。在此过程中,由于黄先生没有新著问世,被纽普兹大学辞退,失去正教授的职位,甚至落到领取社会救济金的地步。
为什么会这样呢?正是黄先生的写作体例与文采出了问题。在《万历十五年》英文版完成时,黄先生几乎找不到出版者。审读专家嫌他独辟蹊径的创作风格离经叛道,学术论说不够深刻明晰。出版社却迷失了对于作品属性的判断:学术出版社说它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写成的,更像是一部历史小说,“全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,而以一位不随俗流的文人在狱中自杀作结。”商业出版社却告诉他:“注释必须剔除,内容要重新编排,让周末住在郊区的白领读者,能够从阅读中放松自己。”黄仁宇先生曾经愤怒地说:这样的评价冲突,“我听得太多了。”[4]
但最终黄先生还是放下身段,在学术与文采之间不再摇摆,而是创造出一条写作新路。结果他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,运用优美的文笔讲述明代故事,获得极大成功。他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共二百八十一页,其中参考书目一百三十四种,注释五百五十五条,再加上附录,共占掉六十五个页码,几乎是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。即使这样,它依然成为畅销书,正如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在书评中所说:他将“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,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,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《长城》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。”[5]
董桥先生非常赞扬黄仁宇先生的文采,他对黄先生文章的评价最为生动。他在短文《窗外一树白茉莉》中写道:“在赫逊河畔纵论中国历史的史学家黄仁宇既写出了那部轰动中外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也写过两部历史小说:《长沙白茉莉》和《汴京残梦》。这两部作品虽然没有拍成电影,黄仁宇却已经先把历史扔出窗外,凭记忆重组历史谱成小说了。他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当然也是这样改编‘小历史’去体现‘大历史’的景观。……中国这么多病痛,给黄仁宇扔出窗外的历史,终于长出了亭亭一树白茉莉。”[6]
四 王充闾的“英雄情结”
王充闾先生散文自成一家,个性鲜明,实为“学者散文“的风范。他擅长几种文化场景的写作,各见优长,各见功力。对此,世俗的评说并不一致。那一天几位评论家坐在一起聊天,讲到王先生作品,有说他游记写得最好,有说他历史散文写得最好。还有一位谈到,王先生各类文章恣肆汪洋,气象万千,实为他旧学功底深厚,支撑他一生不断发力,每每落笔惊风,为今人所不及。但也是旧学作祟,使先生文中时时露出些学究气。可叹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风,成也学术,涩也学术,不可兼顾。只有《碗花糕》一类文章,写得最顺畅,将来必成经典。我非评论家,对王先生文章缺乏异见,只是崇拜。如果说到阅读感受,让我飙泪最多的,却也是《碗花糕》、《母亲的心思》和《小妤》了。 [1] [2] [3] 下一页
|